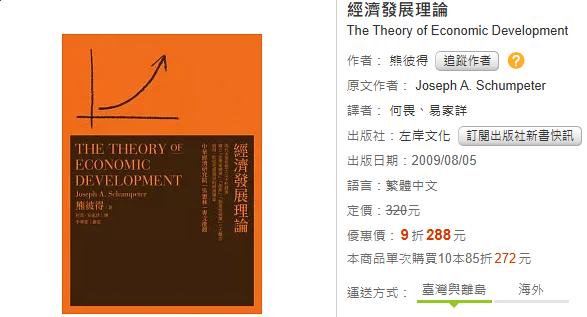
在网上售卖的《经济发展理论》。(网络截图)
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对‘创新’研究有贡献的学者,可见‘创新’的重要性。这也让我想起一九九九年四月,被台湾媒体封为“竞争力大师”的波特(Michael Porter)教授,再一次抵台发表“高价”演讲。尽管被形容“价码高”,但以座无虚席的场景言,可推知向隅者应不少,如此,相对来说,其票价实际上是“便宜”的。真实的市场景况是如此这般,只不过听讲者“事后”是否都觉得“值回票价”呢?这都藏在听讲者的个人心中无法客观得知,但由媒体报导及有些评论,可知波特此行似乎并不像上次带来“钻石理论”算是有创见,而只提出“创新”这个老掉牙的创意名词。不过,由今日诺贝尔奖再度肯定,可知“创新”的历久弥新、颠扑不破,甚至愈陈愈香。那么,“创新”的原创者何许人也,它又是何义?
“创新”理论溯自一九一二年
“创新”(innovation)这个名词的出现,可追溯到一九一二年,在《经济发展理论》(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)这本名著中出现,其作者是鼎鼎大名、已故的奥国学派一代宗师熊彼得(Joseph Alois Schumpeter,1883~1950)。有必要在此一提的是,虽然熊彼得普遍被归在奥国学派行列,但其一些主张其实与奥国学派的传统差异极大,尤其一九三三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教,归化美国之后更是,例如他大力提倡的经济学数理化,就是奥国学派抵死反对的。在二〇〇〇年时,熊彼得还被路透社一项对经济学者调查“过去这几个世纪以来,谁最具经济影响力?”,选为第五名,次于凯因斯(John Maynard Keynes)、亚当•史密斯(Adam Smith)、马克思(Karl Marx)和弗利曼(Milton Friedman),可见其影响既深且远。
熊彼得提出“创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”这种主张,他所谓的“创新”其实就是将各种生产要素加以“新的组合”,以当前流行的经济学术语,就是“不同的生产函数”。所以,所谓的“创新”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函数,使各个生产因素在不同组合下,能创造出更多的产出。由于在任何一个时期内,生产函数都可以表示为依社会在当时的知识水准下,每一生产单位所能使用的技术,因而“创新”往往与“技术进步”同义。
具体而言,“创新”概念包含五种:一是新物品的提出,或对一件原物在性质上作某种改进;二是新生产方法的提出;三是新市场的开发;四是新原料或半制成品来源的发现;五是新产业组织的形成。
对照熊彼得一九一二年的说法,波特和当时台湾台面上与之对谈的成功企业家有没有“创新观点”?答案似乎是否定的,不过,这并不表示他们的谈话内容不重要,也不是说创新没价值。反之,我们可以明显得知,熊彼得早就道尽现代社会如何前进的秘诀,在历经一百多年还能闪闪发光,足见这个理念禁得起考验,是颠扑不破的。二十世纪末二〇〇〇年千禧年,新经济、知识经济响彻云霄,但就其本质内涵,仍然脱离不了创新这个老概念。
历久弥新的“创新”说
其实,不用波特等人再炒这个观念,一般的中外标准教科书中,已白纸黑字将担任创新角色托付在“企业家”身上。翻开任何一本中外经济学教科书,都会告诉我们生产要素可归为四种,一是劳动;二是资本;三是土地等自然资源;四是企业精神。最后一种就是所谓的“企业家”所拥有的特质。一个基本的问题是,劳动和企业家指涉的对象既然都是“人”,为何需要作这样两种不同生产要素的区分呢?若作深一层的探索,其中的确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。不过,如果予以简单化,是可以作这样的区别:劳动指的是有形的、可以量化的劳动数量及其提供的劳务,通常以“人数”或“工时”做为单位,其单位价格或报酬常以“薪资率”或“工资率”称之;至于企业精神的解释就比较棘手,较为通用的解释就是熊彼得提出的创新行为,值得一提的是,必须对“创新”(innovation)和“发明”(invention)作明确区分,前者是发明之中具市场价值者才算,而后者可用“无中生有”称之,此与当前的“研究与发展”(R&D)这个通用词差可看成是同义词。
由于发明原本就不简单,既劳心又劳力,又得耗费其他的成本,进一步要得到市场人士的青睐当然更艰钜了,因其必须冒着偌大“风险”,以及具备对抗“不确定性”的勇气和担当,血本无归的概率是难以估量的,一旦成功当然也应当有较高的利得。,就因为需要具冒风险的无比勇气,并且也要拥有较高的能力,一般凡夫俗子似乎被认为较难做到。即使有勇气冒险,也有发明的热忱,但却屡试屡败,这种人当然无法列入企业家,也不能称其拥有企业精神。准此,标准经济学教本里,就将企业家的报酬特别再以“利润”称之,意义是“总收入减去总成本”,其有“剩余”、“加值”之内涵。当然,我们所说的成本都是“机会成本”,这里所说的利润指的是“经济利润”或“超额利润”,是超过“正常利润”的那一部分(对这些基本名词不了解的读者,可以查阅任何一本当代经济学教科书)。
人人都可以是企业家
经由这样的解析,我们其实可回归到一个非常简单的、但也可能让大多数人费解的观念,此即有能力创造多余利润者就是具企业精神的企业家,如此,不必是大公司的负责人、不必是社会名流,都可以是企业家。换句话说,能创造“多余价值”者就是企业家,所以,全人类的企业家似乎比比皆是,差别的只是程度大小而已,但,我们必须再加上“不以暴力、欺骗、胁迫手段”、或“以光明磊落、诚信伦理态度来创造利润者”就是企业家,其精神就是企业精神。这种认知与已故的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,早在一九六〇年代早期就说出的“企业家只有一个责任,就是在符合游戏规则下,运用生产资源从事提高利润的活动,亦即,需从事公开和自由的竞争,不能有欺瞒和诈欺。”不是大同小异吗?而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作这样的引伸,是否与熊彼得的原意不符,这有赖读者们仔细研读这本《经济发展理论》。
读这本一九一二年的旧作(英译本一九三四年),再对照今日的经济学书籍,不免有所感触,今天的经济学家,虽然也强调“人的行为”,但其实在图形和数学模式的包装下,几乎与“机械人”无异,完全失去了人味,而读熊彼得的书,就觉得有人的呼吸在,特别其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,更是当前经济学书籍所丢弃,但却是极其重要的。因此,很高兴能看到本经典书中译在台湾出现,可是由于本译本出自中国大陆学者,一些用语会让台湾读者多费一番思量,即便如此,其精髓仍然存在呢!虽经近四年后才再版,但在此速食化、不重视读书的时代,这么生硬且不易懂的翻译书得以再版,更证明其具长远价值性呢!
(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)



















